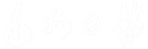20世纪70年代,物资匮乏,小时候,家里很少有花钱买的玩具,但是父母制作的爱心玩具却不少。老妈缝的沙袋、毽子,老爸做的铁环、陀螺等,尤其是老爸巧手加智慧结晶的滑板车,算得上是孩童时代最奢侈也最有范儿的高档玩具。
“孩儿们,老爸要给你们变一个魔术,变一辆——车车儿……”一天,老爸下班回来,手里握着几个黑不溜秋的轴承,带着几分神秘冲我和弟弟卖着关子,还故意把“车”字的音调提高了八度。
“什么,车车儿?”弟弟的声音里明显带着问号,扑闪着一双放光的大眼睛,直溜溜地瞪着老爸。
“对头,滑——板——车”,老爸把这三个字拖得老长。
一连几天,老爸下班回来,都在堂屋里捣鼓着,锯木板,钉钉子,修轴承,轴承里圆滚滚的灰色小铁珠,伴着些许黄油和机油,洒满了一地。我和弟弟蹲在旁边,看着老爸的手上沾满机油,额头汗水“滴答”,梦想老爸的魔术瞬间成真。
果真,第三天傍晚,夜幕降临时,老爸的滑板车终于大功告成。一块旧木板下,安装了三个轮子,前面一个、后面两个。前面的轮子上面,有一根可转动的圆形木条,坐在木板上,双脚可以踏在木条上左右转动借以调整方向。
“整好了,来,试一试!”老爸拿着刚刚出炉的滑板车,领着我们来到宽敞的街头,开始“试车”。
弟弟性子急,率先坐上去,惊喜之中带着一丝胆怯,一双手紧紧握着木板的边沿,猫着身子,生怕摔下去。老爸则在后面,双手搭在弟弟肩上,轻轻一推,滑板车就“呼呼”地朝前滚动起来。
“哇,太棒了!”随着滑板车的加速,弟弟兴奋得尖叫起来,惹得我跃跃欲试。
“后面推车的人,不要用力过猛,要缓缓地……”老爸一边教我们,一边示范。当我小心翼翼地坐上滑板车,老爸示意弟弟在后面给我当助力,滑板车随着弟弟小手的推动,沿着青石板街面,“哐哐当当”朝前滑动起来。
不一会儿,街头挤满了看热闹的小伙伴,他们这里摸摸、那里看看。从他们欣羡的眼神里,我和弟弟瞬间爆棚了一股无法形容的优越感来。
“不能去跑下坡路”“不准到公路上玩”……自那以后,老爸给我们“约法三章”,规定了玩滑板车的一系列规章制度。我和弟弟连连点头,生怕一不听话惹恼了老爸,将珍贵稀缺的玩具没收。
然而有一天,老爸老妈都不在家,我和弟弟便不安分起来,我俩不甘心只在平路上玩滑板车,便偷偷地来到坡度明显的公路上,享受滑板车依靠惯性从高处冲刺低处的“高速度”。任凭风儿在耳边唱着歌,任凭风儿轻抚着脸,一种从来没有过的欢欣和惬意,从头到脚弥漫开来。
“姐,干脆我们一起坐!”“好!”我和弟弟的奇思妙想达成一致意见。弟弟坐在前面,我则坐在后面,咱俩同坐在老爸做的滑板车上,一起往前冲。
耳边风声变得越发急促,滑板车摩擦地面的“嚓嚓”声越发响亮,公路两边的行道树,赛跑般往后退,我紧紧抓住弟弟的肩膀,惊喜刺激中夹杂着一丝不安。由于重量陡增,速度太快,加之惯性太大,快到公路最低处时,坐在最前面的弟弟一时慌了手脚,来不及把握方向,“咚”的一声巨响,滑板车径直撞在路边一块大石头上,一只轴承被撞“飞”了出去。我和弟弟倒在路边,我的裤子摔出一个大洞,弟弟膝盖破了皮还渗出了血。
“不好,车子摔坏了……”我俩谁也顾不上膝盖的伤,都忙着捡拾被摔坏的滑板车,一边捡一边哭。我们心里都明白,伤心的不是腿上的伤,而是心疼那辆滑板车。
那晚,我俩俨然没事人一样,对受伤一事只字不提,只是提着“残疾”的滑板车哭兮兮地找老爸“求救”。巧手的老爸,经过一夜细致地修理,还去隔壁张叔叔家重新找来轴承换上,滑板车顿时恢复了原样。看着修好的滑板车,我和弟弟相视一笑,心里美死了,压根儿忘了腿上的伤。我俩对摔跟斗一事全然未提,直到我和弟弟膝盖上都结了痂,老爸才知道咱俩曾经不听招呼闯祸的事。自那以后,我和弟弟再也没有到公路上玩过滑板车。
时隔多年,这件事仍记忆犹新,老爸的滑板车,更是载满了我们无法忘却的童年欢乐。如今,漂亮、时尚、科技元素满满的玩具比比皆是,唯有记忆中这款“父爱牌”滑板车,弥足珍贵,永生难忘。
□向萍