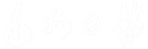羊群从远山归来,羊鞭在手中脆响,羊群沿着鞭响走成一线,在山间路上弯来绕去,仿佛老屋房顶上袅袅升腾的炊烟,不断牵扯着我游移迷离的目光。母亲的呼唤声不断传入耳鼓,我挥动羊鞭,加快了回家的步伐,一颗怦怦跳动的心儿早就坠落在了家门口。
走成一线的羊群依然徜徉在山坳里,久久滞留,像河里的流水忽然被一弯石壁阻隔,兀然没有了先前急速、顺畅、轻快、灵动的流淌……我只好收拢一颗焦急、迫切的心儿,与缓行的羊群同行。慢慢绕过山腰间陡然生出的几块平地,久久踯躅,似若误入荒漠,再也转不出来。羊群却不会被这些缠来绕去、转弯抹角所迷惑,几去几回,几进几出,几穿几梭,如同针线穿过纽扣,它们迅捷地将我从迷宫里带出来,又回归到下山的路径上。
此时我看见,房顶炊烟夹杂着淡淡的青色,淡淡的银辉,缠缠绵绵的,丝丝缕缕的,磕磕绊绊的,在房顶上逗留、飘逸、翻转、飞逝;然后,绕过瓦楞、屋脊、房屋周围的树丛和晾衣杆,直直地扑向一股风路。它们沿着风路奔跑、追撵、狂飙,转眼间,就撞进了林湾深处,横亘出一条耀眼的飘带,纠缠住一阵密密集集、唧唧喳喳的鸟鸣。没想到飘带比鸟鸣更加轻盈,这些零落细碎的鸟鸣,一不小心就从飘带的筛眼里遗落了、漏掉了,只有鸟翅驮起晨露般晶莹的隐隐烟痕,急不可耐地藏身于更远处的草丛间了。
乡村的房屋如同月夜的星辰,零散、简洁、隐约、幽僻,隔溪相望,临竹而围,傍塘挨壁,骑岩跨梁,枕涧抵谷,随径绕滩,跟洼跳沟,挤崖靠桥,村民们借势而建。山村里终是难见几处现成的平地,房屋建成后,不是吊脚就是立柱,山里雾气氤氲,夜间露重潮湿,土墙和木窗正好隔潮挡湿,成为乡村独有的农居景观,别有一番风味。
村庄里,房前屋后总是被果树、花草、灌木、刺藤、丛林和竹荫簇拥,偶尔也见到几棵孤傲的翠柏和不屈的苍松。它们或旁逸斜出于房前的院坝,或青枝绿叶于屋后的林地。房上炊烟从房顶的瓦沟里流溢出来之后,最爱牵手这些草木与枝叶。它们纠缠不休,嬉笑怒骂,暗生情意,然后百转千回,回眸留笑,最后才依依远去,渐行渐远,终是消失殆尽,不见踪影。
偌大的村庄,不但养育了林丛的葳蕤,还呵护了乡村的成长。当飞鸟、露珠、青草、牛羊、雨雪、蛙鸣和虫吟被溪流灌醉,当枯藤、麻雀、蝴蝶、蚱蜢、松枝、柏丫和鸟巢被田泥收留,飞翔于林丛里的斑鸠就会一翅驮起村庄的休憩、顽皮、咳嗽、脾气、习惯和气喘,隐入邻近的鸡鸣和远处的犬吠。这时候,我正好放学归来,趁大人去田地里劳作,我就一个人将牛羊撵到绿草蓬勃的山间。牛羊津津有味地咀嚼着一个下午的美好时光,我则或躺或趴在草坪上,俯视着山湾里一顶顶房舍的瓦间冒出的丝丝炊烟,开始了无端的猜测和遐想。
那梦幻一样绵长细腻的长烟或短雾,有的稀薄,有的浓稠,它们一味地缠绕和飘逝着那些浅草或高枝,肆意地起伏和回旋着那些细芽或粗藤,舒适地铺展和漫卷着那些宽叶和窄须,久久地逗笑、缠绵、嬉戏、打闹、捉迷藏。
我边看边想,觉得那房上冒着浓烟的人家,一定是被亲情包围的人家,儿孙满堂笑语欢,猫狗鸡鸭满屋跑,堂屋里一定坐着一位备受尊敬的老爷爷或老奶奶,他们正慈祥地笑眯眯地看着儿孙们,心中装满甜蜜和幸福;那屋檐已然破旧,房顶夹杂碎瓦的人家,一定是懒散和惰性的,为了躲避劳动,许是去走亲戚赖着不走了,不然房屋四周哪会这样清静和空荡?
我固执地认为,炊烟生得茂盛的人家一定是勤劳、殷实的,烟缕飘得懒散无力的,一定是不懂生活、不善节俭的,每年别人家里还吃着干饭的时候,这样的人家早已青黄不接,落入苦熬日月、吃了上顿无下顿的境地。母亲常说,人要有计划,家要有安排,不然一年四季都会忍饥挨饿。一转念,我又想,这家也许就一个人,出门揽活儿去了毗邻村庄,一时半会儿回不来,是我错怪人家了。可这家人院里院外实在冷清,只剩下几只瘦弱的鸡仔慢吞吞地在屋檐下觅食和游弋……
时光穿过荏苒远年,记忆依然停留在懵懂少年的情怀里。如今,不管身居何处,我始终走不出我的故乡、我的老宅。那纠缠不清、牵扯不断的乡愁宛若老屋炊烟,是母亲缝制的一件棉袄,永远温暖着我的远游和漂泊,将我的梦话和念想一次次揉进内心,唤我回家。
□张浩宗