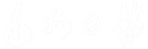我有一个好姐姐,更有一个好姐夫。
姐夫跟我差不多,都是普普通通的打工人;我跟姐夫又差太多,他是一个顶天立地的男子汉,纯爷们。我有点娘娘腔,所以非常佩服他。
姐夫家里有四个兄弟还有一个姐姐,姐姐嫁在广东站稳了脚跟,哥哥弟弟也跟着去广东讨生活了。姐夫排行第三,没有去,选择留在家伺候老母亲。他能吃苦,那时候小煤矿还没有关停,他在附近挖煤赚钱,存了好多钱,娶了我姐。
姐胆子小,婚后不准姐夫去挖煤,姐夫只好去广东江门和他的哥哥弟弟一起当菜贩子,当时没有固定的摊位。那段时间,姐姐、姐夫吃了很多苦,却没有赚到多少钱。后来姐夫考察当地的香厂,广东老板烧香信佛的多,所以香形成了大规模产业链。
姐夫考察完后,回家投资办起了香厂。办香厂是个辛苦活,全厂职工只有姐姐、姐夫两人,既抓生产又抓销售还抓烹饪,青树坪的香贩子都到他家来买香,如果多买了几担香,还要招呼人家喝酒吃饭。
虽说勤劳能致富,但是普通人家一年消耗不了多少香,加上还有同行的竞争,所以销量有限,发财很难。
记得2003年冬天,我退伍回来去姐夫家,那时他还在办香厂。姐夫满身是灰,在给香棍子扑腾打滚,让它们把调好香料的湿香粉子匀称地吸附上去,再端出去晾晒,房前屋后到处晒着香。
过了两年,姐夫就没办香厂了,制香的设备在户外日晒雨淋,生锈了。
姐夫要供两个娃娃读书,上面还有母亲要赡养,经济压力大,他只好放弃当企业家的梦想,跟隔壁老六一起进城务工。先是学着在工地上“装模”,他脑子灵活,学东西快,水电安装都顺带学会了,很快就成了装模的一把好手。
说到脑子活,我要插一个他的小故事。有一年春节在我家打扑克,大部分都是村里的人,当时他们跟姐夫不熟,只晓得是我家的“姑爷”。跟姐夫打牌的有一个人是“牌精”,姐夫最后一张牌,那个人也是最后一张,姐夫说,随便你什么牌,反正我打得起你。那人被姐夫镇住了,乖乖地把牌放下,表示认输。结果被姐夫捏在手心严重变形的是最小的黑桃三,那人气得要吐血。
姐夫已年过半百,在外面务工超过二十年,西部他最远到过新疆哈密,南边他去得最多的是广东东莞,广西、福建、天津、山东他都去过,一般都是住在工棚里。上了正班,他还想办法多加班,想多寄钱回家,撑起这个家。他们家的儿子从小学开始就在镇上读书,姐姐陪读,租房子住,姐夫不拼命赚钱怎么支撑得住?在工地里受了工头的气,晚上就抽便宜的香烟解闷。姐夫不容易,打电话回家开口就是要让明年参加高考的儿子“要考六百多分”“要考个北大清华”,他希望儿子有个好前途,不再重复他受的苦。
姐夫的房子是以前的老房子,房子后面就是水渠,夏日骤雨初歇,水渠的水跑不赢,姐总担心山洪暴发,只得不停地扒拉出水渠周边的草木枯枝,保持水渠疏通。姐夫一直希望在马路边盖新房子,有了新房子就有了面子,大家都是这么想的。
姐姐一心只想培养孩子读书成才,走出大山,因为饼只有这么大,钱只有这么多。他们意见相左的时候,最后都是姐夫听姐姐的,跟我的小家庭一样,女同志地位略高于男同志。
前些年姐夫赚钱多,拿回来的钱自然也多,妈妈的项链、爸爸的戒指都是姐姐买的。我这么笨的人都知道姐姐用的是姐夫赚的钱,姐夫能不知道吗?但姐夫总是憨厚地笑笑,他从来没有过问钱去哪里了。
平心而论,假如妻子把我的钱给岳父岳母买金器,我肯定翘嘴巴,我很小气的,在这一点上,远不如姐夫,需要学习他身上那种男子汉的大气。
姐姐和姐夫结婚后,每年大年初二大团圆的时候,我家掌勺的必定是姐夫,满满的两三桌人,他随便做个菜端到桌子上都是秒光,哪怕是一盘叶子菜。
不是饿,是他烹饪水平高。
炒牛肉辣椒要切成什么样子?炖牛肉怎么掌握火候?做口味鸡,食用油下锅要加热到哪个程度?柠檬鸡爪要怎么调口味?对此很佩服,反正我只晓得拿双筷子,重复一个动作——吃。
等大家都吃完了,他才和我这个打下手的小舅子一起喝杯酒,他总是憨厚地笑着,说一句话笑,喝一口酒也笑,听别人说一句话接着笑。他是一个非常温暖的人,一个很喜欢笑的人,有点弥勒佛的味道。马未都说过,一个人最好的状态,是眼睛里写满了故事,脸上却不见风霜。这话用在姐夫身上再合适不过了。
大年初二的那天晚上,我们围炉烤火,爸爸妈妈也加入我们的聊天中。爸爸不停地装烟给姐夫,爸爸喜欢抽烟,是把烟看得很珍贵的。姐姐提议合影,于是我跟姐姐、姐夫还有他家两个孩子合影,我跟姐夫站在一起,两个年龄加在一起九十多岁的大男人笑得一脸灿烂。
一直认为姐夫是一个顶天立地的男子汉,他在家乡建新房是迟早的事,两个娃娃读书也很争气,他们全家的日子一定会越来越美,我们的大家庭也一定会越来越好。
□刘楚强