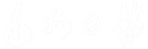在茵茵生长的五月,认识了两种树:广玉兰与山玉兰。
广玉兰与山玉兰不在一处。广玉兰在大学校园宿舍楼前的小道边,钉在树干上的铭牌应该很久了,方形的铁片歪斜着,从锈迹斑斑的褐色里,能清晰地辨认出“广玉兰”三个字;山玉兰在机械馆开阔的草地上,距离过道有些远,需走近,方可分辨出“山玉兰”三个字来。
广玉兰与山玉兰,似乎都没有玉兰花那般富态和妖艳。广玉兰长得高大威猛、粗枝大叶,仿佛一个说一不二的庄稼汉,长势也有些心高气傲,笔直向上,在约三米高时才极不情愿地长出简略的分枝,也是斜逸着向上,仿佛头顶的那片蓝天才是志向和目标。广玉兰的叶肥大如小蒲扇,革质,正面似乎都是油炸过的,深绿中带着焦黄,焦黄里透出油光,背面则是难以看透的灰白。我对广玉兰的叶充满好奇,可惜树实在太高,作为一棵常绿树,树底下实在找不到一片广玉兰叶,否则真要拿起一片来掰扯一番,弄清楚这广玉兰的叶是否如油腻中年男那般不修边幅,是否如乡间炒熟的薯片那般硬脆。不过,这标本式的大叶有些单调乏味,着实少了一些让人把玩的欲望。
广玉兰开花性急,在百花争艳的三月,便按捺不住进入繁花期,兴冲冲地试图和其他花草一起烂漫。不过,广玉兰开的花是另一种面目,与枝叶的邋遢油腻极不相称。硕大的花形如造型夸张的喇叭,一尘不染的白,里外通透的白,这种敞亮而豁达的颜色铺张开来,似乎能闻着浓郁的香气。可以说,在姹紫嫣红的三月,广玉兰花的富态与纯洁,足以在这花花世界中取得一席之地。可惜,大多时候,广玉兰花的张扬被肥大的叶片遮盖,为数不多的花朵只能努力地从叶丛的缝隙中抬起头来,与娇艳的海棠花对眼,与细碎的白梅示笑,与烂漫的樱花颔首。进入葱绿的五月,广玉兰似乎没了兴致,擎着一树老气的枝叶,在初夏的阳光里惺忪如梦,有种过一天算一天的心不在焉。
山玉兰是否原本长在山上,我并不知道,但从山玉兰树的形态和长势上,看不到半点山林的戾气和粗野。山玉兰树比广玉兰树妩媚多了,也没有广玉兰树的傲气,粗壮的树干向上两三米,便匆忙长出结实的枝干,东南西北四处伸展,仿佛空间就是时间,时间就是生命。山玉兰的树冠,如同撑开的一把大伞,茂密的枝叶层层叠叠,漏不过一丝风。山玉兰树叶也肥大,但没了广玉兰的那种油腻,而是薄薄的一大片,让阳光的穿透力轻而易举地照出自己内心的脉络,然后映出一片金色的黄,与自身澄澈的绿叠加起来,变成这个季节里难得的嫩绿,看起来如初春新发的一般可人。我看见山玉兰树,时常以为叶片应该如桑叶般柔韧,握在手里,丝滑如织锦的手绢。
远不止如此。原本以为山玉兰是不开花的。在五月中旬的一天,我经过山玉兰树下的时候,发现草地上全是星星点点的白,以为又是绿化工人种上了某种新奇的花草,弯腰细看,却发现是山玉兰树掉落的花朵。头上有山雀儿喳喳一阵吵闹,抬头才发现山玉兰葱郁的叶间全是点点朦胧的白,仿佛深邃的夜空布满了灵动的繁星,犹如山间平湖中泛起的潋滟波光。山玉兰的花很细,远看如柑橘花,但没有那种黏稠的药香,甚至连半点儿花香都没有。因为,在山玉兰开满小花的树上,看不见蜂蝶飞舞,甚至路过的野蜂都未曾停留。山玉兰的花与庞大的身子极不相称,我暗自疑惑着。
俯身拾起一朵托在手心里,左右端详,一时讶异于大自然的巧夺天工与美轮美奂。是的,这不是花,而是一件艺术品。黄豆大小,没有花瓣,从花梗下拉出几丝花线,然后迅速向内弯成一个弧形,在尾部收束,俨然一个微型的镂空皇冠,精致而高雅。花色并不是纯白的,而是白中带点微黄,更显时光的久远,又如泛黄书笺般隽永。我忍不住在山玉兰树下站定,看细碎的花朵从半空落下,一点,两点……每一朵山玉兰花的落下,似乎都是经过缜密思考的,果断、坚毅、笃定,没有半点犹豫和纠缠。花朵在触碰地面的瞬间,迅速弹跳起来,如一场约定的集体狂欢。
在不经意的五月,我领略了广玉兰的粗野与散漫,也领略了山玉兰的细腻和高贵。其实,在日夜兼程的凡尘,也有很多的广玉兰与山玉兰。
□郭发仔