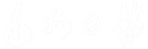整理书橱,发现一叠花花绿绿的布票。愣怔片刻,我才想起,那年从乡下接父母进城,收拾东西时,见木箱里的一本书夹着布票,扔掉觉得可惜,就带进城。我并无收藏爱好,随手塞进书橱,就忘了它们的存在。
多么熟悉的布票啊,我一张张翻看,票额有大有小,最小一市寸,最大十市尺。布票的年份不同,文字图案也各异。岁月远去,它们五颜六色不减,固执地散发着旧时代的光彩,勾起我无尽的回忆。
布票,是计划经济时代的产物。那时物资匮乏,所有生活用品都按国家计划,由供销社统一供应。各种票证应运而生,布票、粮票、油票、肉票、糖票、棉花票、卷烟票、肥皂票等。
票证时代,制衣的布料凭布票购买。叔父在供销社当售货员,神气得很,走路衣襟都带风。供销社掌控物资供应,有实权,巴结他的人多着呢。
我家的布票寸寸计较,但也远不够用。富家后代,财富没能传下来,各种讲究却浸透到了骨髓。祖母大家闺秀,母亲小家碧玉,从小受熏陶,穷得喝浆子,也要鲜衣亮妆绷面子。爷爷是生产队队长,管上百号社员,若衣衫褴褛谁会听他指挥?四个妹妹女大十八变,衣服鞋袜跟着变。我呢,生来爱臭美,上学后更甚。唯有父亲忽视衣着,母亲骂他邋遢,时常帮他打理。所以,母亲老借布票,或拿粮食换布票。虽然家里粮食不充裕,只能勉强糊口,但母亲认为“饥饿事小,体面事大”。
母亲借二妈的布票最多,二妈缺钱,经常用布票换东西。二妈有三个娃,冬天衣不蔽体,手脚冻得像红萝卜,夏天光胳膊光腿,晒得如木炭一样黑。母亲借二妈的布票不用还,给一碗米或一升麦,又或是拣我淘汰的旧衣服给她娃穿。多年后,弟兄姊妹聚会,三杯酒下肚,免不了忆苦思甜,堂弟总会给我敬酒,感激我的旧衣服。
床头边那口彩绘木箱是母亲的陪奁,收藏着好衣服。箱内好衣服不多,平常我们舍不得穿,赶场或走亲戚时,才拿出来穿半天,回家后立即换下,折叠齐整了才放进箱里。为防止衣服被虫蛀,箱里搁了樟脑丸,樟脑丸可驱虫,但驱不了我。母亲下地干活,我就胡乱翻箱寻找硬币,凑七八分钱便去买画本。硬币不常有,布票却常在,总被我翻找到。
布票每年定额发放,人均三五市尺不等,过期作废。最少的一年,人均只发了三市尺,仅够成人做一条裤子。母亲视布票比钱重要,将其夹进一本书里,珍藏于箱底,买布时才拿出来,用剪刀沿空隙处剪开,小心翼翼地,生怕剪坏。
我个子长得快,特别费衣服,衣服洗后缩水,上衣套不了上身,裤子盖不了全腿。母亲只好筹钱买布,给我制新衣,我的旧衣服便给妹妹们穿。至今大妹还翻旧账,抱怨是穿我旧衣服长大的。我费衣服还因为成天在外上树下水,摸爬滚打衣服就遭殃。裤子最先破,前露膝盖后露屁股,露膝盖没人笑话,露屁股却羞死人。有一次滑大青石,屁股突然感到凉凉的,原来裤子滑破了,我只好背着双手遮住破洞。小伙伴们夸我学干部模样真像,哪知我是遮羞呢。上衣则是双肩最容易破,割牛草、扯猪草,背篓天天如影随形,衣服还没褪色,双肩却开洞露肉了。
深夜煤油灯下,在娃娃们起伏的鼾声中,母亲找来布料,熬夜补衣。睡梦中醒来,我常见母亲飞针走线,灯光把她的身影投在墙上,也永远铭刻在我心里。新三年,旧三年,缝缝补补又三年,小娃娃就长高长大了。成人后的我,每每想起母亲挑灯补衣的情景,就心头发热,眼眶润湿。
补巴衣服硌眼,巴不是补在衣服上,而是人脸上。不过,大家都穿补巴衣服,五十步没资格笑百步。因家中长子的优势,我极少穿补巴衣服。
制衣的布,有土布和洋布之分。土布手工作坊织,布面粗糙,颜色单一,非青即蓝,水洗后会褪色。洋布工厂机织,布面细腻光滑,颜色多样,而且不褪色,有各种花卉图案。穿洋布衣服,精神又体面,但价格贵得多,那时的农民一般都穿不起。
我们家爱穿洋布衣服,还买有灯芯绒、华达呢之类的高级洋布衣服。祖母是我们家唯一穿土布衣服的人,老式斜襟长衫,与时代格格不入。她念旧,对土布怀有深情,祖上屠宰业起家,靠织染业发达,曾富甲一方。织染业时期留存下来的织机、染房、染缸等物,成了她炫耀家族辉煌历史的实物。
20世纪70年代初,公社供销社的货架上,陆续出现的确良、的卡、凡尔丁等化纤布料,不褶皱,不缩水,结实耐穿,还有弹性,但价格昂贵,两三块钱一尺,让人望而却步。挣钱犹如针挑土,点灯都怕费煤油,怎敢奢望穿化纤衣服呢?但追赶时尚的母亲,总有办法让家人穿上化纤衣服,引领乡村服装新潮。
母亲明白,年终决算没指望。她挖麦冬、麻玉儿、过路黄等药材,卖给药材收购站;养母猪,母猪产猪崽,最多一胎产十二只,卖了近两百块钱;李子熟了,背去乡场卖,一次也能收入二十块钱左右……除去柴米油盐开支,钱都换成了我们的身上衣。母亲不仅让我们穿新衣,还穿出了时代风尚。那年夏天,妹妹们一身花裙,灿若朝霞,整个乡村好似都明亮了起来。
“制芰荷以为衣兮,集芙蓉以为裳。”屈原穿奇装异服以示高洁,想要超凡脱俗。我也爱臭美,却无法脱俗,见公社广播员穿凡尔丁布长裤,裤管笔直,羡慕得直流口水。我纠缠母亲,说十三岁不小了,说初中快毕业了,各种理由齐上,也要穿凡尔丁裤。母亲悄悄给我十块钱和三尺布票,让我放学后,自己去供销社买布。那时,十块钱对绝大多数农民来说不是小钱。我把钱藏在贴身衣兜,感觉沉甸甸的。我深知这钱来之不易,它浸透着父母的辛劳汗水,不时摸一摸,生怕不小心掉出来。途中遇到父亲去公社粮站送征购粮,我唯恐被他窥破秘密,招呼也不敢打,一溜烟儿就跑掉。
父亲不喜欢土里刨食的生活,但养家糊口压力山大,迫使他把目光投向土地之外。当兵不成,参工没份,从医无门,万般无奈之下,他学了裁缝手艺。裁缝属于农村五匠人员,可以不参加集体生产劳动,但要向生产队交纳定额费用,才能享受社员待遇,参与粮食和财物分配。
拜师学艺两个月,父亲就独立裁剪、缝纫、制衣。当缝纫机像动听的山歌,在堂屋“扎扎”响起时,十里八乡的人,都拿着布料而来。父亲为他们量体裁衣,遇到疑难就翻阅《服装裁剪缝纫技术》。父亲聪明,又勤奋好学,很快就成了远近闻名的缝纫师,顾客越来越多,收入水涨船高。一向骄傲的叔父,自愧弗如。有红白喜事的人家,制衣量大,又要赶时间,便叫人搬运缝纫机,请父亲去家里制衣,好吃好喝,待若上宾。
最忙是春节前,布料堆积如山,天天有顾客来催工,都要在新年穿新衣。父亲没日没夜地赶工,忙得走路带风。母亲将家务活儿交给妹妹们,给父亲当助手,折边、熨烫、锁扣眼、钉纽扣。我也被父亲强按在缝纫机上,干锁边之类的简易活儿。夜深人静,家家入梦,唯独我家灯火明亮,机声不歇。如果没有高考,我大概会子承父业,成为乡村缝纫师。
1979年我考上大学,母亲买了供销社最好的布料,父亲熬夜赶工缝制,的确良衬衫、的卡中山装、翻毛领华达呢短大衣……行走在大学校园,我一身行头毫不逊色于来自城市的同学,唯有脚上的千层底布鞋,在他们锃亮的皮鞋面前相形见绌,举步畏缩。高考前,班主任为我们打气鼓劲,“穿草鞋穿皮鞋,在此一搏。”我有幸搏得穿皮鞋的命,却还没有皮鞋穿。一夜翻来覆去,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,我写信回家,很快就收到汇款,穿上了皮鞋。
改革开放后,布票完成了历史使命,宣布退场。成衣流行,供销社隔壁的服装店生意红火,各种布料、款式的衣服都有。裁缝生意一落千丈,父亲惨淡支撑了两年后转行。父亲的缝纫手艺没人继承,一如祖先的财富没能传承一样。那台蝴蝶牌缝纫机,二妹搬进城,偶尔做些缝补之类的活儿,至今还在效力。
香港回归那年,我接父母进城生活。春节前,妻子给父母买了新衣服。看母亲换新衣服,乐呵呵地像小孩,我不由得想起儿时,情难自禁,鼻子阵阵发酸。
年复一年,积少成多,母亲的大衣柜爆满,不让大家再买衣服,但妹妹们依旧我行我素。母亲很生气,训斥她们乱花钱,伸手打人,但举得高落得轻,打得妹妹们嘻嘻哈哈的。母亲无奈,添了一排组装式简易衣柜,可很快又挂满了。
父母的卧室,像服装仓库。我动员母亲,捐赠部分旧衣服,接济困难的人。曾经受穷的母亲东挑西拣,却件件难舍。
□常龙云