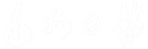疼痛像一株倒生的鸡血藤,每年立春准时破颅而出,在眉骨间盘虬,探出细密的触须扎进血管,把CT室的白光绞成钢筋森林里的蛛网。胶片里模糊的灰影,是钢筋在骨缝里锈蚀的年轮。
缓解病痛的“良方”是母亲手里提着的一大袋药草,辗转三次,走了半个小时路,才到我的手里。接到她时,蛇皮袋里的艾草与紫苏叶正进行着光合作用的迁徙。她眉梢沾着晨露,夸耀着配方,坚信这一袋子草木可以治好我的顽疾。
一踏进门,母亲便着手安排今晚熬什么水给我敷头,明晚用什么方式替我按摩足底穴位。其实她并不懂任何医理知识,连足底按摩也是从小区门口足疗店的广告中听来的,可她信誓旦旦的表情似乎已经确认“良方”一到,必能药到病除。对于母亲的话,我权当耳旁风听听,并未放在心上,于我而言更愿意相信医院的仪器与权威的诊断。我不忍戳破那些混杂着足底按摩与视频里偏方的医理——就像她永远相信,艾草能驱散核磁共振的电磁雾一样。
子夜,疼痛在骨缝里布下蒺藜阵。我如一条被热浪冲到沙滩上的银鱼,张大嘴巴不停地呼吸,骨缝间的触须摇身一变如同万千钢针从鳞片中迸出,疼痛刺激着我的脑神经。那一刻,我仿佛看见了白茫茫的大海上,刺眼的白光比酷夏的骄阳更令我窒息,分不清浑浊的世界里,哪里是海边的盐碱滩,哪里是我可以去的潮汐?药水瓶里细密的气泡从眼角晃过,疼痛的触须遍布四肢八骸。
消毒水的气味突然裂开一道缝隙,涌出晒干的艾草香——我又回到了乡下老家,在乡野的泥土上。阳光亲吻我的额角,溪水在脚下欢唱,草儿的嫩芽拂过裤脚。风漫过山峦,携着山林的清香,一脉一脉地浸润着锈斑的血管。母亲背着竹篓在后山连绵的绿浪中翻找……
母亲推门进来时,我正蜷缩在止痛针编织的幻梦里。她粗糙的手掌覆住我冰冷的额头,掌心残留的艾叶清香漫过我的鼻翼,床前的脸盆里,黑黢黢的水上漂浮着艾叶、紫苏的残渣。氤氲的水汽中,弥漫着浓郁而苦涩的药味,额头的毛巾如三月的暖阳拂去冰冷的寒气,钢针渐渐退化成蒲公英的冠羽,在药香里飘散。她灰白的鞋底上沾着车前草籽,遗留在城市的地砖缝里,扎根、崛起。那些被疼痛割裂的昼夜,忽然被掌心的香气织成香甜的梦。
翌日清晨,母亲把我拽进了老中医的药铺。药铺藏在巷子深处,青苔漫过门槛,木格抽屉吞吐着山野的呼吸。紫苏叶在铜秤上轻轻震颤,三七根须垂落如雨帘。陶罐里正进行着古老的置换反应——人参的皂苷置换我血液里的自由基,鸡血藤的鞣质与CT造影剂发生酯化。
翻涌、蒸腾的雾气中,母亲与老中医交流、比画,我伫立在门外怏怏不乐。母亲走出来,将我拉进屋里,一边向医生赔着笑脸,一边耐心劝慰着我。我想:从小到大,这应该是她第一次如此和颜悦色地宠着我。出门时,淅淅沥沥的微雨中,几大袋“草木”如保命符一般被母亲护在怀里。衣服被草药撑得鼓鼓囊囊,母亲如同身穿布偶的道具人,在雨里踉踉跄跄。望着母亲头顶那团湿漉漉的白发在雨中结出的水晶,钢筋筑就的墙门外,刮入一阵强风,刺耳的风声戳破了心底坚硬的冰锥。在风雨中,我破天荒地挽着母亲的胳膊,把半个身子依偎在她怀里。
回到家,头道药汤泼进瓷碗时,浓苦直冲天灵。母亲在砂锅前守着文武火,身影在水雾中若隐若现,仿佛被洇成一幅写意的水墨画。当第二遍药香漫过窗棂,直冲天灵的苦涩里竟渗出清甜,我看着母亲的背影,仿佛看到她攀着晨露采撷过路黄、夏枯草的画面,听到溪水吻过茯苓的絮语。我走过去,站在母亲的身边,轻声问道:“妈,这药有用吗?”母亲的眼神里充满坚定:“草木是有灵性的,会帮你赶走疼痛。”原来草木的慈悲,是要熬过三遍滚水才能尝到的。母亲的心,却在晨暮中摇曳了二十年。
转过身,我把药渣晒在阳台上。褐色的残叶在春风里舒展,渐渐化作蝴蝶的形状。一日,我发现鸡血藤抽出了新芽,在钢筋混凝土的缝隙里,它替我长出了通往山野的根须。疼痛化作经络间游走的气,推着我去嗅雨后新翻的泥土,去触摸老槐树皲裂的皱纹。
清明那日,我带着药渣上山。松针铺就的软毯上,去年的鸡血藤已开出淡紫色的花。山风卷走掌心的残渣,恍惚间,二十年前母亲背我采药的画面与此刻重叠。原来我们身体里都住着一间中药铺,肝是柴胡,心是莲芯,肺里飘着川贝的雪。当城市的锋刃割伤魂魄时,只有草木记得如何用年轮缝合伤口。
下山时裤脚沾满苍耳,像大地别上的绿色胸针。母亲说该换药方了,蝉蜕该换成夏枯草。我忽然听见混凝土裂缝中有新芽折枝,那些山野的根须正沿着春光的经纬蔓延。原来每阵疼痛都是未寄出的家书,等待某一袋跋山涉水的草叶,替锈迹斑斑的灵魂盖上当归的邮戳。
□青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