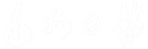1996年11月。
在深圳石岩的一家电子厂,我每天机械地重复相同的工序,努力倾听耳旁的南腔北调,吃水一样的粉汤。
故乡这时已是深秋,而我还穿着夏季的白衬衣和淡蓝色的牛仔裤。早晚时间,我会去厂门外杂货铺供人休息的场地坐一会儿,也会在那里打个电话或写封家书。有时,还会和同车间的一个湖南男孩去镇上逛一圈。那个男孩名叫阿华,比我小,有一张漫画里美少年一样的脸,笑起来没心没肺的样子。阿华比我先进那家厂。那天,我跟在主管身后,避开一张张冷漠麻木的面孔,就看见阿华站在一架床前对我粲然一笑。我还给他一个善意的微笑。
工作中,阿华给了我很多帮助;闲暇时,他也会像尾巴一样跟着我。因为刚进厂,带去的路费已所剩无几,虽然囊中羞涩,但他每次买油粑时都会给我买一个,我去买时也不会忘了他。于是,两个青涩的少年,满足地吃着油粑,站在11月南方的街头,放声玩笑。我情绪低落时,不爱说话,阿华就陪我在夜市上漫无目的地游荡。他总爱一手搭在我肩上,晚风吹乱他的头发,他边走边不停地对我讲话。很多年以后,我早忘了他那湖南普通话的腔调,可他当时说的内容,我至今还记得。他说他的亲戚朋友都在塘厦,春节过完他就过去,让我也跟着过去。最后,他又对我招牌似地笑,“一切都会好起来的”。这话他是对我说的,又像是对自己说的。那一刻,我发现他灰褐色的眼眸里有一抹明净的忧伤,跟我一样。
那天下班后,我准备去杂货铺买个信封。刚出厂门,就看见一个熟悉的背影,那个在我童年时代经常出现,长大后又逐渐淡去的背影。我兴奋地大声喊叫,“伟儿哥”。
伟儿哥是我大姑的幺儿,他要来看我,我爸上次在电话里提过。在那个举目无亲的地方呆久了,即使听到乡音也会喜出望外,何况是伟儿哥,那个在我们大家庭里榜样般的人物,那个在我3岁时给我叠纸帽子,在我5岁时带我去看小人书,在我8岁时教我做暑假作业的兄长。伟儿哥笑盈盈地朝我走来,我们就在杂货铺外找了个空位坐下。
“出门前,舅舅一再叮嘱,叫我一定来看下你”。伟儿哥说。我喝着伟儿哥买来的水,傻笑着。
伟儿哥问我要不要跟他去坑梓,我毫不犹豫地答应了。伟儿哥说,“老家的人都在那里,也好有个照应”。
这时,阿华气喘吁吁地跑过来,“打好饭不见你人,到处找,怎么坐这里来了?”笑着说完,他打量了一眼坐在我对面的伟儿哥。
“阿华,这是我表哥”。
“伟儿哥,这是阿华,这段时间他一直帮助我”。
听说阿华对我很好,伟儿哥自然感激,又买来水和零食招待阿华。
次日上午辞了工,我就回寝室收拾行李。阿华一直躺在我的上铺,没有动静。我以为他睡着了,就没叫他。我背着背包出门,不自觉地回头,看到阿华正趴在床铺上眼巴巴地望着我,充满了忧伤和不舍。我本来雀跃的心跟着也有些黯然。于是,我走回到阿华的铺前,在他摊开的手心里放了五块一元的硬币:“实在找不出什么东西,这个,留作纪念”。
我想,无论什么时候,我们付出的情谊都渴望能得到回应,何况是那样不设防的年纪。阿华先是一愣,然后翻出纸笔,快速写完交给我。我看见上面是一连串的电话号码和联系地址。
“这上面有能找到我的所有的联系方式,深圳的,湖南的……”说着,阿华的声音低了下去。
最后,我们相视笑笑,就像刚认识时那样。在我转身离开的瞬间,我看到阿华的眼里有闪烁的泪光。奔向新生活的是我,当时我不见得有多么不舍。
伟儿哥在厂门外等我。他接过我的行李,我们跳上一辆中巴车,兴致勃勃地离开了那个灰墙铁门的所在。
很多年后才明白,生命里出现的一些人,只能见一次。有些城,也只能去一回。不是不想再见,只是总有这样那样的原因,把我们隔在了那些人、那些城之外。
车到坑梓时已近黄昏。苍茫的暮色里,是一排排整齐的厂房。风,吹得我有些发冷。
转眼我进新厂工作已一个月了。跟原先的厂相比,新厂的环境较差,工作时间长得变态,每天加班到凌晨四点,次日早上七点又要打卡上班。好处是生活在老乡中间,不用说蹩脚的普通话,很自在。
有了吃苦的准备,食堂像猪食一样的饭也能咽下。白天上班瞌睡来得实在不行,就借故去洗手间,有次蹲着蹲着,一不留神就坐到了便池上,幸好便盆里的水是一直冲着的。凌晨回到宿舍,伟儿哥看到我灰头土脸的样子,叹道:“早知这样,就不该带你过来,可能呆在原来的厂还好些。”“你不要这样说,是我自己要来的。”我故作轻松地笑笑。提着水桶去底楼冲凉,去晚了又要排好久的队。睡觉是天大的事,哪还顾得伤春悲秋。
有一天深夜,我还在车间加班。一个小时前,我和一个老乡蹲在原地歇气,被忽然进来查岗的主管逮了个正着,主管不由分说,上来就踹了老乡一脚。因为伟儿哥一个亲戚的关系,主管没对我怎样。但看到瘦小的老乡被踹得一个踉跄,我心里还是忍不住难受。如果没有那点八竿子都打不着的关系,那一脚我也逃不过。正当我独自郁闷时,伟儿哥兴冲冲地一路小跑进来。我知道他是给我送吃的来了,除了油粑,应该没啥别的了。但他却在我面前,变戏法似地拿出一个保温盒。
“从老乡那里带过来的面条,还热着呢。”伟儿哥笑着说。
我欣喜地接过保温盒去了休息室,揭开盖就闻到一股家乡的味道。其实,那面条再普通不过,就是加了葱花,猪油的清汤面,可就是那样一盒面条,却让我怀念了很多年。在伟儿哥含笑的注视里,我喝光了最后一口汤。
深圳的冬天,在寒潮来袭那几天异常寒冷。每天清晨我们穿过长长的堆着木条的厂区,冒着寒气去排队打卡。凌晨四点,披星戴月地走进冲凉的卫浴房。我感觉自己全程都是闭眼完成的。临近春节时,我感冒了,刺骨的风见缝插针地灌进一贫如洗的男工宿舍。同寝室的工友早已跑得无影无踪,难得在那样的生存环境下,他们还能保持火一般的生活热情。我独自躺在床上听歌,头疼欲裂。那年听得最多的是王杰的《回家》,总听得我鼻子发酸。
过完年,又继续开工。伟儿哥托人把我调到了一个工作相对轻松的部门。后来发生了一些事,我遂决定回家。
“要不重新找个地方试试?”
“我想好了,不了。”
知道我很执拗,伟儿哥没再劝我。
“那想好回去做什么?”
“可能,学点什么技术吧。”接下来的路怎么走,我也很迷茫。
领了工资,留足路费。把剩余的钱都留给伟儿哥,知道他那时急需用钱。伟儿哥死活都不肯接。我问,“我们是不是兄弟?”他愣在那里,眼神很复杂。后来,他来信说,一个人在外闯荡那么多年,深知人情淡薄,我让他很感动。
说了不用送,伟儿哥硬要送我去车站,听说车要晚上才走,就先陪我去吃午饭。
“下午就不用来了,车说不定什么时间就走了。”
伟儿哥没有说什么。不过,晚上下班后,他又跟表嫂一起赶过来,陪我去吃了晚饭,然后去超市给我买了在车上吃的零食和水。
很多年以后,我的眼前还能闪现一个画面:伟儿哥搂着表嫂,朝我挥手。四周是一片静寂的黑暗,一切都变得无声无息。
那年以后,我和伟儿哥有好几年没有见面。
2003年去深圳见一个老朋友,顺便去下沙看望伟儿哥。他还是那样神采奕奕,多少年来都没有改变,不管是顺境还是逆境。那天,我穿了件火红的圆领衫,七分牛仔裤。
“变了,很好。”伟儿哥注视我好一阵,才开口说。
万里晴空下,我们都笑了。
□刘成